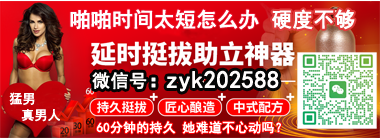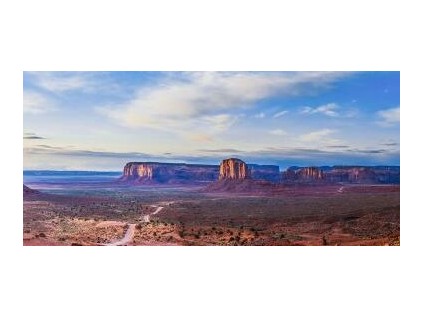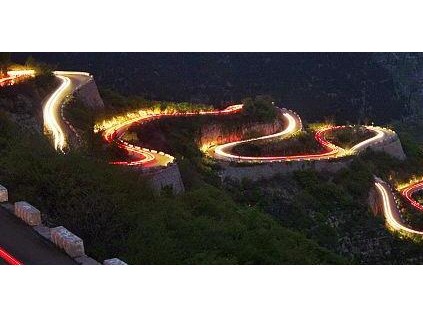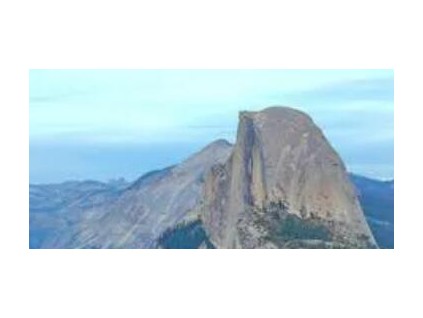《酱园弄》的核心矛盾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。影片改编自1940年代上海“酱园弄杀夫案”,这一真实历史事件本可成为探讨女性觉醒的绝佳载体——长期遭受家暴的詹周氏在绝望中反抗,其遭遇本身已具备强烈的女性主义张力。然而,陈可辛选择将案件置于三段式历史框架下,试图通过时空跳跃构建“女性地位变迁史”,却导致叙事重心严重偏移。
导演刻意模糊詹周氏是否为真凶的核心事实,转而用“杀夫谜团”制造悬念。这种手法虽能刺激观影快感,却剥离了案件背后的制度性暴力本质。当观众被引导质疑“她是否无辜”时,影片试图传递的女性反抗精神已被解构为法律推理游戏。
影片将性别压迫简化为“父权制度VS觉醒女性”的二元对立,甚至通过角色之口抛出“杀夫是女性对压迫的终极反抗”等口号式台词。这种将复杂历史问题标签化的处理,不仅消解了真实案件的悲剧性,更让女性主义表达沦为空洞的政治正确表演。
陈可辛曾以《甜蜜蜜》《如果·爱》等作品证明其对演员的精准把控,但此次《酱园弄》却暴露了其创作团队的严重局限。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被诟病为“符号化受害者”,其龅牙、胎记等造型设计虽具视觉冲击,却未能与角色内心形成有效联结;赵丽颖饰演的进步作家西林更因台词生硬、表演模式化,被网友戏称为“AI换脸式出演”。
雷佳音饰演的伪政府警察局长薛至武,本应是父权制度的具象化代表,但其陨石坑妆容与夸张的台词腔调,使角色沦为脸谱化恶人。这种处理不仅削弱了角色的复杂性,更让影片的批判力度大打折扣。
杨幂饰演的神秘歌女与易烊千玺客串的算命先生,因戏份突兀、动机不明,成为观众吐槽焦点。尤其是杨幂的“番位争议”,暴露出资本干预创作的后遗症——当演员咖位凌驾于角色逻辑之上,影片的整体性便土崩瓦解。